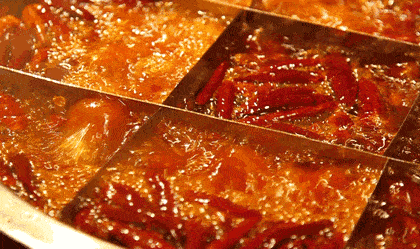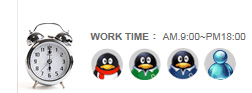火鍋里的碼頭文化
“師傅,,去五里店黃泥村,。”
3月12日,,結束了重慶合川,、北碚兩區(qū)的堪景后,,我回到市區(qū)時正值飯點,,于是打上一輛出租車準備去網紅店黃姐火鍋,。
司機師傅一聽就樂了:“去吃火鍋嗎,?”
“您怎么知道,?”
“外地人都去打卡嘛!”
“那么……‘黃姐’好吃嗎,?”
“肯定好吃嘛,!”他答得爽快。
在寫紀錄片《嘉陵江》有關碼頭文化的這一集里,,我專門提到火鍋的起源,。重慶氣候潮濕,為了驅寒祛濕,,纖夫農夫等體力勞動者就地取材,,在幾塊石頭上架起灶,燃起火,,燒沸開水,,將紅紅的大辣椒、花椒等放入沸水之中,,把食物燙熟之后食用,,便形成了火鍋的雛形。
兩天前,,拜訪川江號子傳承人袁琦時,,他跟我提起小時候在朝天門碼頭“放灘”(游泳的意思),,跟小伙伴游回岸邊后,常會跟碼頭上的船工纖夫呆一會兒,,看著他們架鍋燙一些下水吃,。
“重慶火鍋這么出名,其實最早是船工的吃法,。”他告訴我,。
據說在清代末期,重慶南紀門川道拐的殺牛場宰殺牛羊時,,會把牛羊的內臟扔掉,。住在附近的貧困纖夫們,將這些牛羊內臟撿來煮上一鍋,,名為“水八塊”,。
而重慶火鍋之所以是九宮格,跟碼頭也有很大的關系,。比如說朝天門碼頭,,它位于嘉陵江與長江的匯合處,每天都有大量的物資隨水路而來,,碼頭上聚集著南來北往的人,。附近店家在火鍋中放入一個“井”字型的格柵,不同的陌生人就坐在一起,,使用同一口鍋,,吃著自己格子里涮的菜。久而久之,,這種吃法被保留下來,,它有一種江湖格式在,不拘小節(jié),,豪爽耿直,。
現在,火鍋成為重慶的城市名片之一,,但我并不想僅僅從美食的角度去拍它,。可在紀錄片《嘉陵江》中如何將火鍋與碼頭的關系展現出來,?在什么樣的場景中拍攝,?又是誰在吃火鍋?我?guī)е@樣的疑問,,借著堪景的名義前往黃姐火鍋店,。
黃姐火鍋店
在重慶,大街小巷坡上坎下都開滿了火鍋店,,之所以選擇去“黃姐”看一看,,是因為當地朋友告訴我,,不同于連鎖店的標準化,它的江湖氣還在,。當天運氣好,我竟然沒有等位,,在一堵墻前,,支起一張折疊桌,坐在一張塑料凳子上,。
“牛肝,、鹵肥腸、豬黃喉,、鴨血,、老豆腐 ……”我裝作熟客的樣子,根據朋友發(fā)來的信息,,報上菜名,。
“要得,要得,。”記下菜單的大姐麻利地招呼起后廚,。
當創(chuàng)作要“接地氣”成為一種方向,使我對“美”的概念有了新的理解,。那些肥腸,、毛肚盛在一個個小小的不銹鋼盆碟里,身后是用蛇皮袋拉起來的墻圍,,我坐在這樣的火鍋店里,,竟吃出一種感動,那種看似不和諧的搭配,,卻刻滿生活的痕跡,,透出一種自信與不想改變的倔強。我寫水運,,寫碼頭,,寫的是變遷,但總有某種不變的東西,,而這些不變的內核和基因,,才是讓我更想在紀錄片創(chuàng)作中捕捉下來的。
重慶朝天門碼頭
我多么希望能請到過去航運社的船工們聚在一起,,在江邊一間四壁空空的屋子里,,涮著火鍋聊嘉陵江上的往事,屋里有一扇面江的窗,,能讓人看到江水奔流,,過往如煙,。